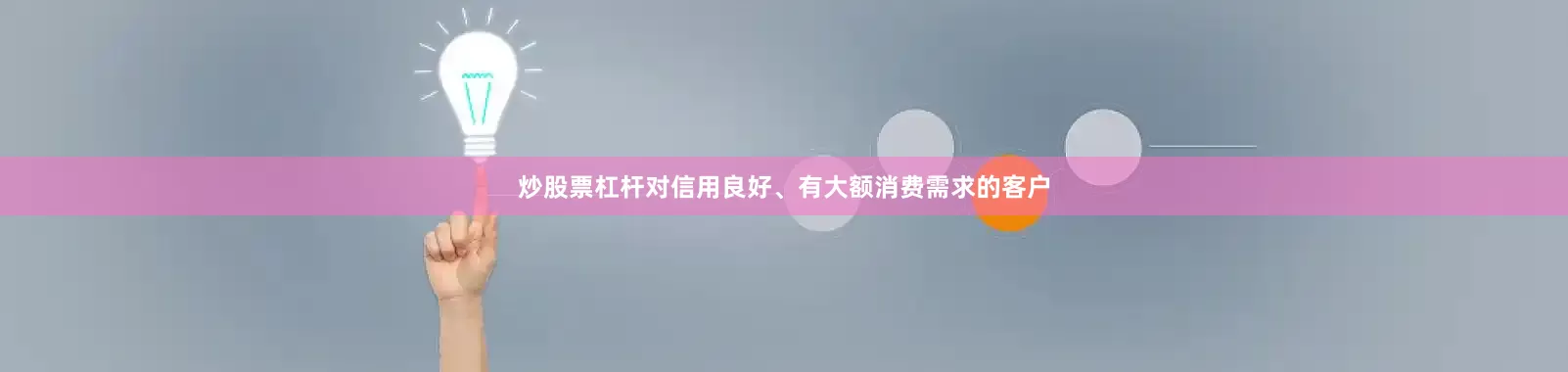编者按:
2025年5月8日至6月9日,由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以下称“北仲”)、北京市律师协会(以下称“市律协”)、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仲裁文化推广月成功举办。开幕式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称“海仲”)副秘书长兼仲裁院副院长杨帆以“认识仲裁文化的共性与个性 树立仲裁文化自信”为题作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如何理解仲裁文化
文化是一个极为宏大的范畴,关于它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无论何种定义,都十分宏大。对于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是“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理解是,文化和文明一样,具有多样性,受到一个地区客观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以及民族性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文化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在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当地的人文、文明交织融合,逐渐稳定下来并传承创新,不断发展。
具体到仲裁文化,它是在仲裁制度的基础上,随着仲裁规则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演化、创新,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是制度、理念、精神、传统等多层面的综合。我国现代商事仲裁制度,严格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从1956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称“贸仲”)成立、我国正式开始现代商事仲裁实践算起,到现在将近70年;从1995年《仲裁法》实施算起,今年正好满30年。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累积,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探讨、思考我国的仲裁文化,正当其时、意义深远。
中国仲裁文化的共性与个性
我国的仲裁文化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从共性来看,仲裁有很强的国际性,因此其文化必然具有开放和包容的面向。我国涉外仲裁制度的雏形和贸仲、海仲的规则与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高效灵活、专业公正等仲裁的基本理念、内生的文化基因,在后来制定的《仲裁法》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并在我国的仲裁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深深扎根。
那么,我国仲裁文化个性的一面是什么?又有哪些特点?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这种从外部引进的仲裁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后形成的我国仲裁文化,一定是融合的产物,也是我们的创新和对丰富国际仲裁文化体系的贡献。仲裁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国际化和本土化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
下面,我选其中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就是仲裁制度与秉承“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理念、崇尚“和为贵”的文化基因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后的产物,是我国仲裁文化的一个独特创新。因为传统和文化的差异,最初这种“东方经验”在西方多受挑战和质疑,但如今,越来越多西方的国家和仲裁机构开始接受这种理念和做法,并加以吸收借鉴。这一创新模式值得我们系统总结,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仲裁与调解的衔接机制也在不断发展。海仲近年来积极与专业调解机构合作,探索“调解+仲裁”的争议解决新模式,2023年成功处理近千件调仲对接案件,高效化解社会矛盾。北仲近期出台的《调仲对接快速程序规则》,也是一种融合创新。这些都体现出我们在仲裁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
第二,我国的机构仲裁文化发达。我国是典型的机构仲裁,这是仲裁制度引进后与我国重机构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当时所处仲裁发展阶段的历史选择,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机构仲裁文化在我国发展非常成熟,机构管理案件的制度完善、经验丰富,如仲裁机构的全过程管理制度、经办秘书制度、核阅制度、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等;在制度建设、规则创新、实践发展、仲裁宣传、人才培养等方面,仲裁机构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我国仲裁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那么,现在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呢?我注意到临时仲裁已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从自贸区的先行实践到《仲裁法》最新修订草案的内容来看,有条件、有限度地引入临时仲裁已是大势所趋。临时仲裁是仲裁最初发展阶段的形态,也是当前发展阶段与机构仲裁并行的模式,至今在国际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海事海商领域,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临时仲裁仍是该领域纠纷仲裁的主流模式。从统筹国内与涉外法治、提高我国作为国际商事仲裁新目的地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引入临时仲裁有其必要性,不仅可为当事人提供更多选择空间,而且对我国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推进海事仲裁规则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回到文化层面,相较于发达的机构仲裁文化,我国缺乏临时仲裁的制度经验和与之相应的文化基础。临时仲裁引进后,与我国实际、文化传统相结合,会形成怎样的仲裁文化和特色,与既有的机构仲裁文化将如何碰撞和融合,非常值得我们持续观察和研究。
树立仲裁文化自信
最后,我想强调,仲裁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值得被系统梳理、妥善保存、大力弘扬。我们也应当树立对自身的仲裁文化的自信。希望“仲裁文化推广月”的活动能够持续开展,越办越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道正网配资-道正网配资官网-散户股票配资-配资查询114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